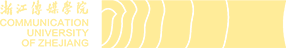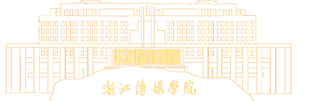“三個臭皮匠,,頂個諸葛亮”體現(xiàn)的是集中的智慧,,集體的力量;而《烏合之眾》中卻說“群體中可以累加的一般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,?!蹦鞘欠襁@樣就可以判定這兩種觀點(diǎn)是對立的呢?我認(rèn)為不能簡單地認(rèn)定一種結(jié)果,,《烏合之眾》本身對“群體”的剖析就是多面,,復(fù)雜的,,它所闡述的觀念與“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”產(chǎn)生的本質(zhì)爭執(zhí)是,群體產(chǎn)生的效應(yīng)是正的還是負(fù)的,?而這個問題,,需要我們辯證地去看待。
首先,,《烏合之眾》中即使有很大的篇幅說的都是群體的弊端,,但是對于群體的力量還是給予了肯定:“以后的社會,不管根據(jù)什么路線進(jìn)行組織,,都必然要考慮到群體的力量,,這種力量是至高無上的,是最終必然會留存下來的,?!睆倪@一點(diǎn)上來說,我們討論的兩種觀點(diǎn)就不是完全對立的,,他們的共同點(diǎn)就是都肯定了承認(rèn)了當(dāng)群體聚集的時候是會產(chǎn)生不可估量的力量的,。只不過,“三個臭皮匠”體現(xiàn)的是能推動事物發(fā)展的力量,,《烏合之眾》里的“群體”,,體現(xiàn)的是不確定的,可好可壞的力量,。
那么基于這個共同點(diǎn)之后的分流,,就是這兩種觀點(diǎn)的對立所在?!叭齻€臭皮匠頂個諸葛亮”是群體作用產(chǎn)生的正面效應(yīng),,而《烏合之眾》中群體產(chǎn)生的往往一種破壞性的力量,只有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才會發(fā)揮積極的作用,。這兩種觀點(diǎn)的分歧體現(xiàn)在勒龐對“群體的情緒”和“群體的意見”的闡述上,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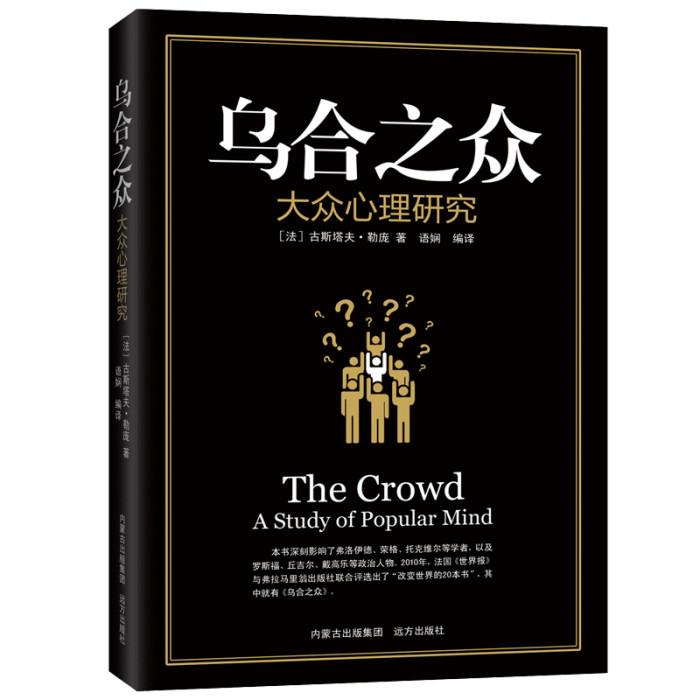
我們可以從最近的“新疆棉事件”來看群體的感情?!稙鹾现姟分姓J(rèn)為,,群體是急躁、沖動,、易變的,,易受暗示和輕信,群體的情緒是夸張與單純的,。新疆棉引起的民眾對事件中涉及的幾個國外品牌的一系列抵抗行為,,本來是一種環(huán)境刺激下自發(fā)地表達(dá)愛國的行為,但這種沖動越聚越大,就超出了可控范圍,,上升到了對品牌下的工作人員的人格攻擊,,我認(rèn)為這就體現(xiàn)了勒龐所說的“在感情與理性的沖突中,感情從未失敗過,?!边^激的行為超出了理智的范圍,此時群體帶來的影響就成了負(fù)面的,,對社會并沒有什么積極作用,,甚至是在給問題增添問題。如果“三個臭皮匠”的意見是在受刺激因素支配的情緒之下形成的,,那么他們除了情感的偏激,,是沒有產(chǎn)生與“諸葛亮”對抗的力量的,他們的聚集只是在累積群體的副作用——情緒發(fā)泄,。
“群體中的每個個人只是把他們擁有的共同的尋常品質(zhì)集中在一起,,那么這個群體所擁有的只能是明顯的平庸,而無法創(chuàng)造出新的特點(diǎn),。”所以,,反過來,,如果“三個臭皮匠”這個群體創(chuàng)造出了他們個人無法產(chǎn)生的才智,集中的是契合群體的個人身上的不凡之處,,那么此時這個群體就起到了積極作用,,產(chǎn)生正面效應(yīng)。
此次新疆棉事件中有過激行為的人們,,就可以看做這“三個臭皮匠”,。他們是中國人,在情感上都傾向中國,,使他們在心理上成為一個群體,,希望自己能發(fā)揮一點(diǎn)作用,群體的情感支配著他們,,如果只是將大家激動的情感累積起來,,那么極容易變成一場抵抗過激的情緒發(fā)泄?!安焕碇恰眲t是他們“共同的尋常品質(zhì)”,,集中起來也就無益處,群體就不能產(chǎn)生正面效應(yīng),。
新的群體時代,,群體的力量依然值得謹(jǐn)慎,只有正確地使用群體的力量,個體形成的是一個優(yōu)質(zhì)的群體,,才能實(shí)現(xiàn)“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”,,相反,就只能給社會帶來一群烏合之眾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