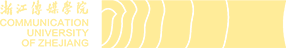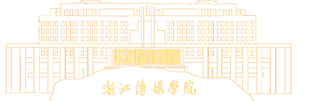隨著科技的不斷發(fā)展,,越來越多的企業(yè)開始使用辦公APP,以這一種更為“現(xiàn)代”的方式來管理員工,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,,企業(yè)微信活躍用戶人數(shù)突破6000萬,覆蓋了50多個行業(yè),,企業(yè)數(shù)量超過250萬,,涵蓋了中國五百強企業(yè)的80%。除以企業(yè)微信為首的辦公類APP之外,,微信,、QQ等社交型APP,“小猿搜題”“U校園”等學(xué)習(xí)類APP在人們的生活中也同樣常見,。近幾年興起的短視頻APP,,據(jù)2019年互聯(lián)網(wǎng)報告,中國短視頻APP日均使用時長增長到了6億小時,,截至2019年7月,,抖音每日活躍用戶已超過3.2億。
從日常聊天溝通依賴的社交軟件,,進(jìn)行線上學(xué)習(xí)必備的學(xué)習(xí)軟件,,到與我們?nèi)粘I钕⑾⑾嚓P(guān)的生活娛樂軟件,我們的生活因這些應(yīng)用軟件而更加便利,。但與此同時,,眾多的APP及其推送內(nèi)容也使得手機內(nèi)存頻頻告急,如山的社交壓力也壓得我們喘不過氣,。那么一個問題便在我們心中徘徊不去:如此多的APP,,究竟對我們而言是減負(fù),還是增負(fù),?
網(wǎng)課背后,,軟件泛濫
疫情期間,或許很多人都獲得了“在家上課”的新奇體驗,。有網(wǎng)友也在微博上調(diào)侃道,,“在被窩里上課的夢想終于實現(xiàn)了”。但是在上網(wǎng)課的新奇感消退之后,,網(wǎng)絡(luò)授課背后的問題不斷涌現(xiàn),。
許多同學(xué)便表示,由于各科老師要求不一,,他們經(jīng)常需要下載不同的軟件并在其中切換使用,,有時一天要切換使用三四個甚至五六個不同的軟件。這不僅暴露了軟件功能不足的漏洞,,并且軟件過多也會造成需求者的使用困難,。
課程設(shè)計專家方柏林便表示:“學(xué)生對于學(xué)習(xí)APP的技術(shù)條件和熟悉程度參差不齊,而支持的部門又沒有,,都靠老師自己忙乎,,手忙腳亂,甚至需要家長幫忙,,這自然影響了教學(xué),。”
但新聞與傳播學(xué)院的張博老師則持有另一種觀點,。雖然借助APP線上授課會對教師教學(xué)水平的發(fā)揮造成限制,,但APP也有其優(yōu)越性:學(xué)生們在平臺上提交的作業(yè)可以保存,便于之后隨時調(diào)取,,紙質(zhì)版的作業(yè)不易留存且沒有備份,。網(wǎng)絡(luò)平臺能夠使學(xué)習(xí)信息化,讓教學(xué)模式更加適應(yīng)大數(shù)據(jù)時代,。
網(wǎng)課教學(xué)在解放了老師和同學(xué),,給予他們一定自由的同時,卻也給他們造成了負(fù)擔(dān),。其目的是減負(fù),,而卻因技術(shù)上的漏洞和不完善之處給學(xué)生和老師們增負(fù)。

“鴿子精”與“焦慮癌”
在有緊急通知時,,我們時常會抱怨收不到通知的“鴿子精”,,但是因為擔(dān)心收不到通知而頻頻查看手機的“焦慮癌”也并不鮮見。
這種焦慮源于信息時效性的特點與工作高效的要求,。參加了四個社團(tuán)和組織的佳佳說,,自己就有很嚴(yán)重的信息焦慮,需要時不時看手機,,生怕錯過什么重要通知,,白白錯失機會。不止是接收通知的人,,有時管理者身上的信息焦慮現(xiàn)象反而更加嚴(yán)重,。一位班干部在受訪時坦承自己出于對工作負(fù)責(zé)的需要,時不時地就要拿起手機查看微信,生怕落下通知,。這種焦慮讓信息收發(fā)者都變成了網(wǎng)絡(luò)上的“驚弓之鳥”,,一見到軟件右上角的小紅點,便情不自禁地心跳加速,,唯恐錯過任何一條信息,。
有時這種信息焦慮則是社交壓力下的產(chǎn)物。受合群心理的驅(qū)使,,人們不愿錯過與自己相關(guān)的任何一條信息,。李同學(xué)便表達(dá)了這種社交壓力下的恐懼,她如此說:“有時頻繁地打開微信并不是因為擔(dān)心錯過重要通知,,翻閱所有的未讀信息只是為了更好參與群聊,。”
當(dāng)然,,也有一部分同學(xué)在受訪時表示自己平時不會有信息焦慮,,他們認(rèn)為生活中緊急通知畢竟還是少數(shù),只要合理安排時間就可以規(guī)避這種焦慮,。
為了消除社交距離的隔閡,,人們選擇積極加入朋友的對話中。這當(dāng)然是在為社交活動減負(fù),,但人們過分在乎消息而至焦慮時,,這卻是在為自己增負(fù)。

砍價的魔力,,社交的壓力
聊天窗口中出現(xiàn)“幫我砍一下吧,!謝謝”的對話,并隨后附上小紅包和砍價鏈接,,這種現(xiàn)象我們早已司空見慣,。在大部分購物軟件上,“分享砍價”的營銷策略屢見不鮮,。上至砍機票火車票酒店訂房,,下至打車買醬油,即便自己不參與消費,,朋友或是家人發(fā)來的砍價鏈接也總會出現(xiàn)在聊天對話中,。
有人認(rèn)為,“分享砍價”對人際關(guān)系產(chǎn)生了消極消耗,,被分享人有時因為維持社交的需要,,不得不幫助他人進(jìn)行砍價。而且往往這些所謂優(yōu)惠力度并不大,,需要數(shù)量較多的被分享人聯(lián)合幫助才有效,,這只是在浪費被分享人的時間和精力。而站在商家的角度,這類分享鏈接相當(dāng)于廣告牌,,鏈接被分享的次數(shù)越多,,越容易讓潛在消費者認(rèn)識它的品牌,利用推薦產(chǎn)生的信任感,,激發(fā)潛在消費者的需求,。
但原本用于購物的APP,卻在社交中頻頻出現(xiàn),,當(dāng)人們收到分享鏈接時,被分享者往往礙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絕對方的請求,,而選擇幫忙砍價,,很多人為這種非自愿的選擇而苦不堪言。

非自愿的選擇,,不斷出現(xiàn)的砍價鏈接,,都是人們自愿或者非自愿之下的“增負(fù)”。
增負(fù),,還是減負(fù),?
即使我們抱怨使用各種APP給我們增添了種種負(fù)擔(dān),似乎名為“減負(fù)”實際上卻還是“增負(fù)”,,但毋庸置疑的是,,各類APP的確為我們帶來了學(xué)習(xí)、工作,、生活上的種種便利,。
借助“抖音”“快手”等短視頻APP,可以完成娛樂場景的轉(zhuǎn)換,,例如疫情期間的“云蹦迪”便滿足了人們對線下娛樂的需求,;在出行方面,“滴滴出行”“攜程旅游”等APP有效節(jié)省了人們的時間,,便利了生活,。“一鍵出行”“一鍵訂餐”“一鍵娛樂”等生活方式成為常態(tài),,人們的生活更為豐富,、方便?!発eep”“運動校園”“陽光晨跑”等運動型APP,,成為高校學(xué)生、就職青年追求健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。

而事實上,,技術(shù)無所謂善惡,只是一種中性的工具和手段,它為人類的選擇和行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,。但是技術(shù)最終產(chǎn)生何種影響,,還是取決于其使用者。各大應(yīng)用軟件作為一種外界工具,,使用者們應(yīng)該學(xué)會如何使用并善用它們,,讓它們更好地為生活服務(wù),而非將自己的生活約束限制其中,,感到受各軟件拖累而產(chǎn)生的“束縛感”,,為自己“增負(fù)”。